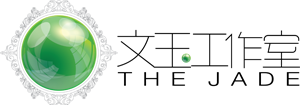文 / 谭思懿
有个很老、很旧的梗——
那时候马来西亚的旅游业兴起,越来越多人改行或入行当导游。当朋友群中有人说:“我也要去做导游了咯。”就会有另一个人很快速地接道:“你做导游,我还做酱清咧”。
这是一个福建方言的梗,普通话的“导游”和福建话里的酱油(福建方言作“豆油”)是谐音,同样读作 dǎo yóu;“酱清”则是“豆油”的同义词。
我在以福建话为主要方言的地方长大。后来,因为上大学,就来到了把酱油称作“豉油”的城市。说真的,我一开始还真有点文化消化不良。这个城市,其实还有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人。因此,当我因为自觉广东话说得抱歉,在日常沟通中尽量使用华话的时候,把“豆油”换成“酱油”召唤而来的不是每次都会是生抽,就像有一次我竟然拿到了老抽。

图片来源:Photo by Caroline Attwood on Unsplash
对于酱油,不同方言语系的人就会有不同的叫法,就像回忆中的那道酱油鸡。一家有一家的味道,一家调不出另一家的味道,而你其实也不会渴望另一家的味道。
对于酱油我是有种偏执的,这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了。那年,难得到离家两百多公里以外的地方旅行,住在二姨家。吃着二姨煮的饭菜时,我说:“二姨的豆油没有这样好吃欸,二姨,你应该买跟我家里一样的。”
这当然不是我自己记得的,是妈妈后来告诉我的。那是因为懂事后,每年至少两次要帮二姨代购半打的酱油,等她来我们家时让她带走。我好奇二姨千里迢迢买酱油的原因,搞得好像吉隆坡没有酱油卖一样,妈妈说:“因为吉隆坡找不到这个牌子的。”后来,我亲自证实了,这儿没有卖这个“豆油”。
来到这座城市以后,我终于明白小时候 TVB 电视剧里演的村姑,为何进城的时候都要带着一大袋通称“逃难袋”的东西,因为我也成为了那类“村姑”。每趟返乡,我就会张罗一堆用品,带回宿舍。同学问我:“你做么要这样辛苦带这样多东西搭火车哦?这些东西你不会在这里买咩?”我都傻笑着回答:“唉呀,家里带来的是妈妈给钱的嘛,省钱呐。”真的只是因为省钱吗?也许答案只有心知道。脑,它不懂。
看着厨房架子上摆好的酱油、黑酱油、麻油、料酒、蒸鱼酱、蒜油……我知道,这是心安的感觉。在离家近 300 公里外的宿舍里,我总是试图做出和家里一样的酱油鸡。我家的酱油鸡称为“乌鸡”,在福建话里是“黑鸡”的意思,我想是在形容烹煮后的颜色。这道“乌鸡”是从前经营经济饭档的外婆的拿手家常菜,和一般认知上“酱油鸡是咸的”不同,“乌鸡”在咸中还带些许砂糖的甜。也许这样听起来会让人难以置信,疑惑带甜味的菜肴能不能下饭,但它确实是我们家族上下大大小小都很爱的“乌鸡”,尤其是小孩。
吃着妈妈的“乌鸡”长大的女儿们,后来也都嫁了人,有自己的家庭和小孩了。阿姨们都把“乌鸡”的煮法学了去,煮给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们吃。后来的后来,连年轻美丽的表姐也结婚、生孩子了。结婚后的表姐,变得超爱下厨。她总在社交媒体发布自己“作品”的照片,并把它们集结成“食物日记”。表姐“食物日记”里的菜色,非常符合新时代家长为孩子选择食物的标准——少糖、少油、少盐、营养均衡。在充斥着紫薯和糙米饭的页面中,我冷不防看见那一碗黑油油的“乌鸡”。图解中,表姐写道“妈妈跟外婆学了煮给我吃,我跟妈妈学了煮给儿子吃”。
是的,回忆就是回忆,没有原因。记忆中的味道,其实无关食材是不是有机的、摆盘能不能美观、吃了可以取得多少营养、会不会增胖……就只是,那个味道。那个——你想复制,却每次都觉得少了点什么的——味道。就好像宿舍里我亲手煮的那碗“乌鸡”,用了和家里一模一样的“豆油”和调料,却始终和家里吃过的那碗不同。最后,我试着安慰自己,也许只是因为掌勺的掌心温度不一样吧。